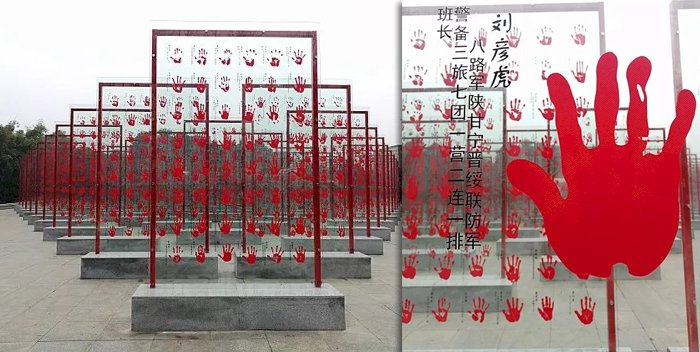7
文革前奏「社教」運動,父親被抽調到農村對口幫教。家中人口已達五口,他一個人收入維持家用已感吃力。
毛澤東一生都沈迷在尋找並企圖消滅他的假想敵的死結裡——可能是同黨戰友、政黨對手或帝國主義,甚至他的人民。未奪政權,他渴望殺敵奪權;奪得政權,他害怕失去權力。他懼怕別人像他當年造反一樣推翻他。這是所有獨裁者的宿命,也是專制制度癌癥所在。他頻繁製造政治運動,摧殘所有人,其實就是在找尋內心的安全感,他哪來作為人的幸福和快樂。中南海其實就是毛澤東自我囚禁的墓地,或許借助於古代帝王的餘威,他晚上才能睡著覺。
文革肇始後的前五年,我家尚住在慶陽地區行署所在地西峰鎮(現今慶陽市),這也是我的出生地。我大約三、四歲時的一天,母親後衣襟拽著我和姐姐、懷抱妹妹,路經城中心小什字。突然遭遇武鬥兩派開打,母親將我們掩在懷裡,就近躲在馬路邊木頭電線桿後面。子彈嗖、嗖直飛,打在木電線桿上,木屑唰、唰掉下。
這就是我降生後,新中國給我刻下的第一個清晰印記。我上幼兒園,老師教我們的第一課,就是用玩具槍玩殺敵遊戲。權力者的敵我階級意識,通過社會、家庭和學校強制植入每個人大腦,沒有寬恕、仁愛、平等和正義等人文教育。
固然,早期中共在少數精英領導下,從中國底層社會隱秘發育,受到極度壓制和摧毀,因此,他們對支撐統治權威的財富和知識的仇恨,滲入骨髓。一旦奪權,對代表財富和知識擁有者的工商業者、地主和知識分子,強制實施社會主義改造,當然也是以期消滅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強力挑戰者。
費正清指出:「無產階級是一個虛構的概念。」「無產階級專政實則是中共對所有人民實行人治。」人民被劃分為幹部、工人和農民家庭出身,貧農、富農和地主等階級成分。血統論和階級論,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最為野蠻和囂張的表達。他們控制所有國家機器還不放心,還要管住老百姓的衣食住行,譬如,辦理結(離)婚證,出差或探親住宿旅館,必須出具單位(或村委)蓋公章的證明,出省還需帶上全國糧票,這實際上是管制老百姓的隱私權和人身自由。
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,即為「社教」失敗,龐大的行政官僚不聽話,和幻覺中的敵人帶給他的不安全感。於是他繞過黨政體制,發動並利用無知的紅衛兵造反,試圖打倒並摧毀一切。十年文革,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殘暴的革命實踐之一。前有斯大林,後有柬共(紅色高棉)波爾布特、朝鮮金家政權——他們與人民為敵,大肆殺戮,將反人類獸性表露無遺。
8
隨著文革深入推進,老幹部靠邊站,父親被支派到山區糧管所工作,我家也被趕出公房,母親帶著五個孩子搬住在窯洞裡。中蘇「珍寶島之戰」和「林彪叛逃」,激化毛澤東的好戰性格。「深挖洞,廣積糧,備戰備荒為人民」,城市人口被強制疏散農村。
在我讀小學一年級那年,一輛載運糧食的「解放牌」拖鬥卡車,搭載著我家全部家當和幾口人,被遣往慶陽縣赤城公社白馬大隊,臨時落腳在大隊部獸醫站後院破敗的地坑院窯洞。土炕泥竈,油燈照明,深溝挑水飲用。

2019年12月,作者重訪40多年前下放的甘肅省慶城縣白馬鎮白馬村壑口組(原慶陽縣赤城公社白馬大隊壑口生產隊),與69歲原生產隊長、退伍軍人楊振武及其妻重逢。
下放疏散就是十多年。父親在白馬糧管所當保管員。夏秋驗收公糧。期間也在壑口生產隊當駐村幹部。我家還保留城市戶口,在糧管所買麵買油,除了沒地耕種,其實跟農民沒啥兩樣。北方農活我都會幹。最刻骨銘心的是,在學校因家庭出身、衣服補丁比同學少,受到老師和同學歧視。初三隨父工作調動轉學驛馬中學,我給自己改名叫劉憤世,初中畢業證赫然書寫。1994年在海南入獄,警察抄家,將我的初中畢業證、中學大學日記本、學運照片等物扣押,迄今未還。
父親的工作在幾個公社糧管所間調動。父親在哪裡,家就在那裡。每次搬家,都借住在老鄉的窯洞裡。
漸漸長大,我們問父親為什麽不回城?父親常常沈默不言。在我的記憶裡,什麽該做,什麽不該做,父親從不會苛責打罵我們幾個孩子,可能跟他中年成家有關。與其說父母讓孩子自由成長,還不如說,他們沒有精力管教我們,任由我們兄妹五人野性長大。
父親率身垂範,要我們做正直、誠實的人。寒冬長夜,父親常在家庭會議上念叨,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供養我們五個孩子高中畢業,他超額做到了。每天兩餐,一張小飯桌擺放在窯洞廚房泥地中間,四周擺上小板凳,全家一起吃飯、交流,建立長幼平等和自由關係。下放期間,兄姐先後插隊當知青,然後被政府安排工作。
1984年全家返城,住進糧食局家屬院。父親也年屆60歲,到了退休年齡。他堅持工作兩年才延期辦理離休手續。離休後閑不住,他又擔任街道居委會黨支部書記。常常召集黨員老頭老太在家裡客廳學文件、讀報紙。母親因我1989年入獄罹患心臟病,需要靜養,於是父母常鬧口角。母親不幸於1994年59歲早逝。當時我第二次「因言獲罪」,在海南島坐牢。

父親離休後使用的特供證,特供香菸和豬下水等。這些特供品在1980年代後期已非稀缺品,隨處可買到。
1989年9月,小妹陪著65歲的父親,從千里之外隴東,輾轉抵達設在山區的甘肅省勞教所探望我。那天刮著大風,我正與其他犯人在籃球場篩煤,滿臉黑灰,饑腸漉漉,哢、哢地咳嗽。走出勞教所三大隊大鐵門,父親和小妹遠遠站在一排颯颯搖擺的楊樹下,大風刮起了他們的衣角,黃塵撲面。
我站在親人面前,咬著嘴唇,說不出一句話。父親沈默。小妹在旁邊嚶嚶哭泣。管教在旁邊看守。過了好大一會兒,父親破例遞給我一支香菸,平靜地問:「你咋不給家裡說一下?!」我參加學運從未告訴家人。

2002年5月,父親在環澳門遊遊船上。
2002年,我讓父親和家人赴深圳遊玩。除了1950年代去過雲貴一帶征兵,這是父親幾十年後再次來到江南,也是第一次乘坐飛機。
一天,父親點名要去深圳蓮花山瞻仰經濟特區設計師鄧小平銅像。鄧小平下令「六四」屠城,而我參與那場民主運動,被投進監獄並開除學籍。76歲的父親拉著我的小外甥女,拾級而上。陽光赤灼,父親滿臉汗水,恭立在鄧小平像前,靜靜地擡頭仰望;我背向銅像,倚靠在石欄上,眺望自由香港。此刻,我與父親都若有所思,卻是多麽背道而馳!
兩輩人的信仰如此不同。多年來父親試圖說服我放棄異議言行,但最終還是失敗了。好在時間可以療治傷口,我與父親,彼此寬容、妥協和尊重,才維繫著濃濃父子情。

上圖,2006年作者與父親在家中。下圖,2009年8月,父親遭遇拆遷迫害,在西安住院期間。
2005年11月,我第三次入獄獲釋後返家探親。回家剛坐定不久,父親即拿出一個褐色木盒子。原來這是抗戰勝利60周年、中央軍委頒發給參加抗戰軍人的紀念勳章(健在的國軍抗戰軍人無此殊榮)。我能理解,這是父親作為一個抗戰軍人最為自豪驕傲的功勳認可。我當時想,如果當局真正關心抗戰軍人,那就提供維持他們尊嚴的生活福利。
父親平靜的晚年生活,終在2009年被打斷。家屬院面臨拆遷。慶陽市政府派出市、區老幹局等各路人馬,上門動員父親搬遷。稱父親作為老革命、老黨員,要帶頭配合城市規劃。甚至匿名打電話威脅父親,如不按期搬遷就停發離休工資。他們避而不談如何解決後續住房。而以父親當年每月四千多元離休金,也無力購買高價商品房;其次,按照國家離休幹部待遇規定,要由政府解決住房。

2006年春節,父親在慶陽市東湖公園。
一波波政府和拆遷辦人員,輪番登門,恐嚇威脅,軟硬兼施。父親帶領家屬院住戶,阻攔推土機停工,但是,卻無法掙脫政府人員戴給他的「老革命」、「老黨員」大帽子。父親維護政府面子,從未告訴家人他因心理壓力大引發陳疾的實情,終於被摧垮住進醫院。父親昏迷在病床,每天全靠十多瓶營養液維持生命。醫生多次下發病危通知。家人已通知外地親戚最後一次探望父親,並著手準備父親的後事。
在父親被政府迫害、生命垂危的關口,他所維護的政府和一生愚忠的黨,早已遺忘了他。這到底是誰的悲哀?但我明白,這是父親在共產制度下必然的結局。

2016年父親臨終前留影,佩戴中央軍委頒發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和70周年紀念勳章。
父親終於從死亡邊緣堅強地復活過來,這年他已85歲高齡。家屬院被鏟為平地。父親自後租房居住,保姆照顧他的日常生活,他不願意與子女合住在一起。
父親臨終前一個多月,我陪伺在側。生活尚能自理,頭腦清醒,還在寫日記。一次,我拿他身份證去醫院開藥,順便給自己開了治腰疼藥。回家後我告訴父親。他責怪道:「占那點(國家)便宜幹啥?!」父親醫藥費全額報銷。母親在世時的治病費用,父親不讓在他名下報銷。現在的官員,不貪腐就是「好官」,早已丟棄早期共產黨人的純真信念和清廉作風。
在血肉戰場,父親剛強如鐵,從不曾屈從死亡;而他曾用生命誓死捍衛的黨,卻在他的晚年,無情地將他摧殘,居無定所。
2016年8月19日22時20分,父親因患肺癌在家中安詳離世,享年92歲。
如題記中所言,此文意在廓清父輩共產革命的荒謬,不僅是寫父親,而是書寫他們一代人的悲劇性命運。
(全文完)
2021年6月,父親節定稿
新聞引據:採訪
撰稿編輯:新聞編輯